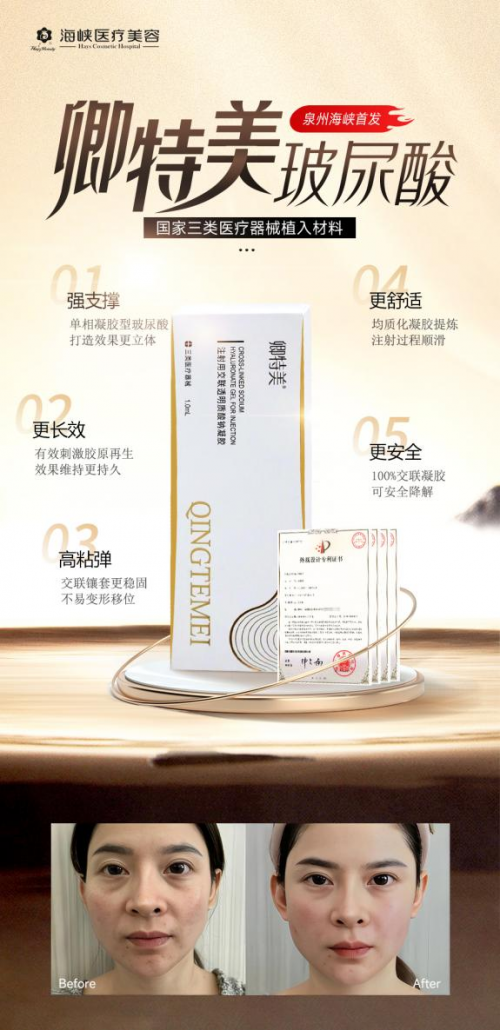影评 & 精神分析理论视域下的奥噶和麦卡——《人工智能》的变奏
一、引言
电影《人工智能》改编于英国作家奥尔迪斯1969年发表的短篇科幻小说《永恒的夏天 :寻求母爱的人工智能男孩》,由好莱坞著名导演史蒂文·斯皮尔伯格指导拍摄,在2001年搬上大荧幕,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反响。这个故事和电影中给人们带来了无限遐想的空间,也带来人们对于“伊托邦”的深刻反思。
电影是以一个不确定的未来世界为背景的,由于气候变暖,海水猛涨,可供人类栖息的地方十分有限,于是美国便选择实施计划生育计划控制人口增长来维持国家的繁荣,大量的机器人取代了各种繁琐的工作,而大卫就是众多机器人中的一个,但是他有了一个特殊的功能,拥有着被称为“灵魂”的感情——无法停止的爱。影片中大卫是在一个儿子患病,也就是实际意义上的失独家庭中,用来慰藉父母的存在。但是这个机器人有个不可逆反的程序,就是一旦启动就无法关闭,除非被销毁。在妈妈莫妮卡启动以后,这个原本看起来融入的“新”家庭被患病儿子马丁的苏醒所打破,马丁对于大卫分享他的母爱是十分嫉妒的,于是在发生了几次“陷害”之后,莫妮卡一家最终决定抛弃大卫。影片的后半段则是围绕大卫为了获得母爱而开展的冒险旅程。
整部影片中所折射的亦是人们的“精神家园”,通过大卫这样一个悲凉的底色,来对发达工业社会中人类异化导致的人性以及除物质外第二世界心灵和第三世界思想的深度思考。人类异化归根到底还是人类在“精神家园”中的迷失,纵观整部电影,镜头的荒诞离奇、童话色彩的浓厚,魔幻与现实的结合,将人物的心理矛盾与变奏进行了复杂的演绎。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中,对人的内在心理进行了分析,作为精神界的哥伦布,发现了精神界的奥妙所在。所以本文将结合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来对影片中人物以及虚幻的“伊托邦”进行分析,挖掘影片中的新大陆。
二、梦幻与压抑:奥噶与麦卡的身份转换
在《人工智能》电影的“伊托邦”中,奥噶和麦卡的身份是发生了转化的,这样的转换是通过反讽意味的奥噶与麦卡心理意识的对比来体现的。影片中第二幕的出现带给我们的就是莫妮卡在抛弃大卫时口中的“外面的世界”,人分两种,一种是真人奥噶,一种是机器人麦卡。奥噶是“organism(有机体)”的简称,麦卡是“mechanism(机械)”的简称。
按照弗洛伊德的分析法,在人的心理活动中,意识是作为心理发展的最高层次而出现的,只有人才会有意识,而在这部影片中,麦卡大卫同样也有了人类的意识,他的潜意识里只是想获得母爱,对母爱的付出丝毫不亚于人类的感情,而且这种感情是最真挚的。在莫妮卡的家庭中,当原本的儿子马丁回来之后发现大卫分享了他的母爱,于是设计陷害大卫,让大卫吃菠菜导致线路板损坏;让大卫去偷偷剪妈妈的头发,结果被爸爸亨利发现,受到了敌意。但这些依旧没有影响在马丁过生日的时候大卫给他送去的生日礼物。
在机器屠宰场中碰到了保姆机器人,她看到大卫的还是孩子便母性显露将大卫抱在怀中,保护他免被惊吓直到她被销毁的前一刻。这也与奥噶的莫妮卡在面对马丁和大卫时,选择抛弃大卫形成了身份转换。机器屠宰场这一段是触目惊心的,这些所谓的没有身份的麦卡被奥噶当众销毁,当然手段包括“捆绑分尸”、“浓硫酸”等等。“我们是活着的,这是一个生命的庆典,这是对人类未来应尽的义务”在屠宰场主持人说出这段话时背后其实更多的是人们对真实生命的忧思。
由此可以看出奥噶的“坏”与麦卡的“善”所形成的强烈对比,在心理意识方面,人类引以为傲的“爱”的意识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消失殆尽,反而机器人成了这些“爱”的意识的物质承担者。
大卫在流浪的过程中遇到了乔,在未来世界里连性服务都可以是机器人,而乔就是一个拥有多功能的“经验型”男妓,在去往“艳都”的路上乔与那些男生的交流“我们专门为你们提供欢愉享受”、“我们的技巧比任何人类都高明”;以及艳都的入口设计成的“女生张着大嘴”的形状,整个“艳都”的设计都是提供“慰藉”的场所。弗洛伊德在他关于梦的定义中阐述了在压抑情况下的欲望表达,满足性欲的主题,当然这个场所也是由原始性爱的本能演化而来,但是奥噶在压抑之下寻找到了新的途径和方式——解决性爱的对象是机器人“麦卡”。
整个“伊托邦”就是人类梦幻构造出来的虚幻空间,按照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中关于梦幻的定义,其实就是一种压抑的欲望,放在影片中就是“伊托邦”作为人们受到压制时所想要表达出的欲望,就像每销毁一个麦卡就会引起台下观众的欢呼,寻找性爱“慰藉”就去艳都找妓师,这些人已经在潜意识里把自己当成了社会的上帝。这些人通过幻想把自己变成新的现实,在“伊托邦”中满足自己的本能需求。
三、“俄狄浦斯情结”的主体变焦
在弗洛伊德看来,人的本能就是“性”,男孩的“里比多”对象则是他的母亲,也就是他的理论中非常重要的学说之一的“俄狄浦斯情结”,亦即“恋母情节”。俄狄浦斯的说法弑父娶母,讲的是希腊底比斯的英雄俄狄浦斯,在无意中杀死了生父,并娶生母为妻。
而且在弗洛伊德看来这种情节是普遍存在于人的深层心理之中的,比如在《俄狄浦斯王》、《哈姆雷特》等作品中,这一倾向十分明显。弗洛伊德之所以认为我们会对这些作品产生共鸣是因为我们潜意识里有一种特质,而这种特质就是俄狄浦斯情结。
在本部影片《人工智能》中同样是建立了俄狄浦斯情结,并通过此情结来推动影片的叙事的发展。从大卫被激活之后,他的潜意识里出现的就是对母亲付出所有,为了得到母亲莫妮卡的爱而不断的学习人的生活方式;真儿子马丁回来之后,为了重新获得母爱去吃菠菜、听马丁的话去偷偷剪母亲的头发等等都是为了占有母亲的爱,在俄狄浦斯情节中同样是对母亲的占有欲。影片的后半段大卫去找蓝仙女把自己变成真人更是为了能够重新获得母亲的关注和爱,因为他坚信变成真人之后就能像马丁一样被莫妮卡视为宝贝,不会被抛弃。当乔跟大卫提到父亲亨利的时候,大卫说“因为亨利不喜欢我”,父亲这个角色在大卫的潜意识里是排斥的。这种俄狄浦斯情节贯穿了整部影片,也是能把整个剧情串联起来的本能动力。
但是影片中大卫最后并不是“弑父娶母”,所以这也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俄狄浦斯情结”,也并没有真正的完成。纵观整部影片就可以发现,“俄狄浦斯情结”是进行了悖反化的主体变焦,重点不在对父亲的“弑”和对母亲的“娶”,也不在于对母亲压抑的“性”冲动,而是通过大卫对母爱的占有来体现的,也就是我们说的狭义上的“恋母”情节,即儿子对母亲的依恋。
当然这里的主体变焦不仅仅是主体所采取方式的变焦,还包括奥噶和麦卡在心理上的变焦,传统意义上的麦卡是一个机械体而已,没有任何的情感,“俄狄浦斯情结”的载体应该是奥噶这一人性身份,这才符合弗洛伊德的研究。但影片中则采用了变焦的方式,即将“俄狄浦斯情结”的载体换成了麦卡,一个有人性情感的机械体,这一观点看似离奇,但又是“俄狄浦斯情结”的真实写照,具有双重意味和艺术魅力。
当然这样的双重意味的结局是在情理之中的,影片的一开始,霍比教授在办公室跟同事们探讨“感情机器人”的问题时,一位女同事提出的“人类会用真爱来回应他们吗?”霍比教授并没有给出答复,而是用“这是一个古老的道德问题”来回避。而影片的走向也正是如此,人类并没有选择用“真爱”来回应,才有了大卫在“俄狄浦斯情结”作用下对莫妮卡的付出,在海底等了两千年依旧想找到蓝仙女成为“real man”,但是这一轨迹注定是重蹈覆辙的悲剧,“俄狄浦斯情结”也注定是一种悖反的主体重建。
四、三重人格下的心理构建
弗洛伊德将人的心理结构划分为三个层面:意识、前意识、潜意识。在1920以后他又对自己的理论进行了调整,即“本我”、“自我”、“超我”的人格结构的重新组合。“本我”是最原始、且与生俱来的非理性的本能和欲望,属于潜意识范畴。“超我”是道德化和理想化之后的“自我”,在人格的最顶层,属于“良心”和“理想”部分,对人的行为进行控制。而“自我”是介于“本我”和“超我”之间,调节两者的冲突和矛盾。
正常情况下,这三种人格结构是相互协调的,但维持平衡并不简单,“本我”的原始欲望会影响“自我”,这时“超我”就要对其进行压抑,一旦失去平衡,人的性格就会出现混乱。
在《人工智能》这部电影中,大卫的心路历程就是在这三者之间不断的交织,在经历各种事情之后,实现了自我身份的重新构建,也得到了成长。
首先是本我,本我是与生俱来的冲动。在影片一开始,大卫被莫妮卡激活时,就得到了与生俱来的想要得到母爱的想法,虽然这种想法是设定的,但是对于拥有感情的机器人来讲,已经与奥噶没有区别。随着影片的进行,大卫被母亲莫妮卡丢在路边之后,便踏上了寻找蓝仙女之路,在本我的欲望的指引下,任何事情都不能阻拦他去寻找蓝仙女,即便是在水下冰封了千年。在找寻蓝仙女的路上,大卫到了“世界的尽头雄狮流泪的地方”,才发现这是霍比教授的阴谋,自己并不是与众不同的情感机器人之后,转身用台灯将眼前的另一个自己砸烂,自已一跃入海,这些疯狂举动就是大卫潜意识里的本我。
其次是自我,自我是处于本我和超我之间的,而且是通过学习社会环境的发展,既有一部分来自于本我,又有一部分受制于超我的限制。影片中大卫想获取母爱的时候所做出的行动,就是自我的体现,也通过了几个细节可以观看出来,在马丁回来之后,大卫为了获得母爱而强迫自己吃菠菜,来证明自己像个正常人,结果损坏电路板;之后马丁又让大卫去莫妮卡的头发,虽然大卫有点反抗,但还是照做了,因为马丁说这样可以得到莫妮卡的爱,但结果被亨利以为他要杀人;在两个人都跌落水池之后,他为了得到莫妮卡的原谅,给莫妮卡写了很多的信。大卫不断的调整学习自我,成为一个真正的人,以此来得到莫妮卡更多的爱。
最后是超我,超我是道德化和理想化的自我,随着社会的准则和价值观念而对自身进行了指导,让自我控制本我的冲动,追求完美,潜意识里按照社会上接受的方式来要求自己。影片中的最后,大卫在冰封的海底被外星人找到,外星人读取了他的记忆后,决定变成蓝精灵帮助他实现这个愿望,他们只想大卫快乐。大卫得到了这个机会,虽然只有短短的一天,而且也不能告诉莫妮卡这一切,但这一天是他最快乐的一天,这一天莫妮卡心里只有大卫一个人。在理想化的自我下,大卫给莫妮卡做她最爱喝的咖啡、一起画画、捉迷藏、开生日派对,成为莫妮卡心里完美的儿子。
当然影片中的人格心理发展不仅仅存在于大卫身上,在马丁、莫妮卡身上也能看到弗洛伊德的三重人格理论。马丁各种陷害大卫也是在本我的冲动的支撑下发生的。莫妮卡在送大卫返厂的路上出于心软,也就是在三重人格中不断的调整,最后在自我的心理影响下,并未把大卫送去销毁,而是抛弃在森林里并告诉他离真人远点。当然机器屠宰场的那些人和艳都里的人都是在原始本能冲动的支配下来获得快感,摧毁机器人的盛大狂欢以及在艳都中形形色色解压的色彩,可以说都在不断的进行心理人格的转换。
五、结语
本文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分析了《人工智能》这部具有双重意味的伊托邦电影,既是科幻又是童话的电影本身就具有神秘的味道,加之主人公又是“麦卡”这一特殊身份的特色,却有着“奥噶”的人格心理,大卫的整个成长历程完成了从本我到自我再到超我的转变,就更值得我们对其进行思考。未来伊托邦里的“麦卡”也在不同社会发展现状的影响下构建自己的人格结构,形成离奇复杂又符合常理的精神世界,也正是因为如此,《人工智能》这部电影散发着永恒的艺术魅力。
参考文献:[1]贾伟程.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之下的魔幻与现实——电影《燃烧》的再阐释[J].戏剧之家,2020(31):131-134.[2]秦磊.浅析《红字》中丁梅斯代尔的“俄狄浦斯情结”[J].名作欣赏,2020(27):149-151+156.[3]陈秀春.电影《人工智能》中的科幻议题与童话演绎[J].电影新作,2019(01):140-143.[4]刘庆华.从斯皮尔伯格的三部电影看人性的失落[J].电影评介,2012(15):23-24.[5]周晗. 人类未来命运的忧思[D].广西师范大学,2008.[6]赵宪章《文艺学方法通论(修订版)》,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
文/王桂岭
编/肖洋
本文图片均来自网络
标题:影评 & 精神分析理论视域下的奥噶和麦卡——《人工智能》的变奏
地址:http://ai.rw2015.com/szyw/9216.html
免责声明:人工智能网为网民提供实时、严谨、专业的财经、产业新闻和信息资讯,更新的内容来自于网络,不为其真实性负责,只为传播网络信息为目的,非商业用途,如有异议请及时联系站长,本网站将立即予以删除!。